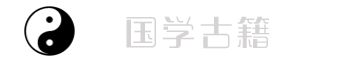历史是个动词,现在进行时
“互文性”,一个新概念
胡适是否回避了“历史是什么?”这一问题?其实并不那样绝对,在胡适的比喻中,一定程度上还是可以读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,虽然他并未提出“观念创造历史”这样直截了当的观点,而是认为“实在”有着人造的形式,而“小女孩”的比喻,也可以从实在角度理解,因此,可以说,胡适对于实在的看法是,“实在”虽是“实在”,但受到我们创造性的影响,由于这种影响存在,过去(这里可以指作为“历史”的实在)并非已经结束了的确定性存在,而是有着开放的未完成的形态,过去有我们(现在)的主观参与、介入。
这样的认知,当然是对“绝对客观”的质疑,对客观规律性的质疑。
这样的质疑,就是实验主义的精神气质,是其挑战理性主义、历史决定论(波普意义上的)的思想勇气的组成部分,它形成了20世纪思想界的主潮,改变了整个欧洲的思考方式与思维氛围。
这一点,可以从历史学内部的反响看出。
美国历史学会主席、著民的左翼学者(亲苏)E·H·卡尔在其《历史是什么》一书中就明确提出“客观的历史并不存在”,但他对此结论不得不有所保留,“这和否认真理的存在不是一回事,这种否认会毁灭判断标准的任何可能性,使得研究历史的任何方法就像任何其他方法一样是真实的。或者……是虚假的”,由此,他提出一种“中庸”的认知:
在这里可以维持客观真理的存在,但是没有哪位历史学家,哪个历史学派能够希望达到这个客观真理。哪怕是一点点接近和一部分接近都不可能。
卡尔认为,事实中立的说法是基于世界持有理性的自由观点的产物,是19世纪的观点。而他的观点是:历史是历史学家与过去的一场“永远的对话”(在本书中,我将使用“互文性”这一概念来表达这一对话过程。互文性,包括主客体之间的互文、历史写作本身内部的互文,以及“过去——现在——将来”的互文三个层次。互文性概念并不是否定历史这一客体的存在,而是强调“历史以什么方式存在?”这样一个操作性话题,这就是我说的通过“话题转换”来拯救思想论争中那些无效又无益议题的思路)。
卡尔说,“在过去和现在之间存在着双向的交通,现在是由过去铸造的,然而又不断地再现过去。”还说,历史是“历史学家与跟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,是现在跟过去的永无止境的问题交流。”
这都是谈互文性。
动词“历史”的历史
也就是说,“历史是什么?”的客观性问题,是一个19世纪特有的问题,科学主义时代的独特焦虑。这,无论是在西方史学脉络,还是本土传统,这样的焦虑都没什么重要性(但并非没有)。
这里先就本土传统对此做一简单梳理。
《说文解字》:“史,记事者也,手又指中,中,正也”。
这条解说明确界定了史的动词性,其中还特别注明此字“从手从中”,这按照汉字六书的构造原理,则“史”表示一种以手记录某事的行为是毫无疑义的。关键在这个“中”的解释。晚清以来的小学家(文字学)认知不一,有释“中”为策,简策之策的;有说是“簿”的,簿记之簿。著名的甲骨学者罗振玉依据江永《周礼疑义举要》认为,“簿”与“中”的关系,是因为“治中”的官职即掌管簿记,如《周礼秋官》中“断庶民狱讼之中”。日本京都学派创始人内藤湖南则将“中”解释推进一歩,以为与射礼相关,射礼中有“凡射事饰中舍筭(算)”,即计算射中的数目。“筭”是竹简,而“中”则是盛简的容器(投壶之类)——这一解释与王国维相同。
由此看来,“史”多少有些后世所谓秘书的意味,只是此后的分工尚未达到当时的细密。如《史通》所说,“至于三代,其数渐繁,案《周官》《礼记》,有太史、小史、内史、外史、左史、右史。太史掌国之六典,小史掌邦国之志,内史掌书王命,外史掌书使乎四方,左史记言,右史记事。《曲礼》曰:‘史载笔,大事书之于策,小事简牍而已’。”
这也是章学诚“三代以上,记注有成法,而撰述无定名”的意思,这“成法”就是一套工作规则,也就是上文所提及的各史各自不同的职责,其所载记之“本事”是什么,取决了这套规则的约定,“事”变化无穷,难以掌控,而规则却是固定的,是可掌控的(这正是“故事”的最初意义,下详)。
说到底,“史”就是这种秘书工作,因当时官府活动留下的这些文献由其记录保存,所以也就被称作“史”,这就是史的名词化,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史也就是这个,但它毕竟是次生意义上的,作为动词的“史”才是第一位的。
这一点,从“史”之对词“诵”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出。
《国语·周语》有一句“吾非瞽史,焉知天道”,是瞽史对举,按“瞽献曲史献书”的说法,可知上古时期“文化”工作是按此两类分工的,具体而言,就是文字化的记载与口语化的传诵两途,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讲,口语化的传诵应该早于文字化的记载,因此瞽史对举而瞽字在前。《史通·史官建置篇》说“前史之建官,其来尚矣。昔轩辕氏受命,仓颉、沮诵实居其职”,这里的“沮诵”,其职务是讲述传授往事,往往由盲人担任(正如传史诗的荷马),故《国语·楚语》有“矇不失诵”, 矇或写作瞢,瞢瞽同义,它也有着严格的传承脉络,如《庄子·大宗师》所说:“闻诸副墨之子,副墨之子闻诸洛诵之孙”。
也就是说,“史”本来具有口传与文字的双途流播,但此后则是文字记载几乎一党独大,这当然与文字及记载材料的稳固性有关。而其胜出口传的具体时段,大约可以推断在汉初,我们知道,当时的经学,还都是由“博士”口传的,如秦博士伏胜百岁还在传其所业(一般认为与秦焚书有关,但如果没有沮诵传统,一火之下,哪来的二十九篇传言?)。此后由于竹简的大量使用(国家工程),口传系统才慢慢被书写系统代替并胜出。
这是从官史角度看,“史”不仅是“记事”,且还有“讲述”,这个“史”,当然是动词。
如果从民间从角度看,则与“史”对举的是“故” (上面提及的瞽史口传并非完全消失,而是流入民间),“史”走书写系统、走官方一途,“故”走口传系统,走民间一途(湘方言谈故,有讲古一说,讲古即讲故)。《说文解字》释“故”,是“从古从文”,也就是说,“故”也是关于过去的记述。依据《现代汉语词典》的解释,则“故”还有死亡、原来、古旧等义项,比如故智、故旧、故习、故实、典故、故态、故我等等,而“故事”的本意,就是指延续下来的行事制度,例行公事等等,如“虚应故事”,这里的“虚应”,并非我们现在理解的虚构,而是态度不够严谨,就如现在流行的“玩忽职守”“戏说历史”。
清理出这些脉络,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,现代人理解的历史,与其起源意义的“历史”有着很大的区别,这一区别在于,现代人将历史当做名词,当做某种固定的物化的东西,而起源意义上的历史是一种记载传诵,是一种行事,是动态的,这也是我说“历史是个动词”的原因。
如果从传诵这一更古老的历史生产传播途径看,历史就更是当下与过去的互动,是传诵者与先贤的互动,同时也是传诵者内部的互动,这种互动是多重的,是动态的,这种互动也就是我说的“互文”。
历史的这种互文性,并非我的发明,古史家们早有表示,如《南史》(十七)说:“旧者非旧,因新以成旧者也”,也是强调这种互文性——新与旧是相互建构的,强调对待而立,而非独立。基于这种认知,“历史”的地位就绝非像我们当下那样被看重,故《南史》中甚至有这样的说法:“陈迹敷陈,尽在鬼箓,过去之事,何足挂齿?”(《南史·扬子津传》)。
从《南史》这种新旧对待互动视角看,我们所谓的过去的事实,就必然是与当下情境相关的,这也符合王夫子“物不孤,必有对”的说法。换句话说,“过去”并不能独自存在,过去只有相对于当下、未来才存在。或者,过去不过是当下的自我表示。换句话说,历史是现在的我们对过去的呈现,因此,历史是一个动词,且处在现在进行时态。这样,我们就将“历史是什么?”这个客观主义问题转换为“历史以何在方式呈现?”这样的主客互文的陈述,一个无效的提问因此也就得到了有效的救赎。
为什么一定要转换提问方式?
“历史是什么?”或许是永久的焦虑,困扰着每个现代人,但这样的困扰并非来自“历史”自身,而是我们认知方式造成的。如果不改变我们的认知方式,这样的困惑就将如幽灵般地骚扰着我们,而至于永无安宁。故,转换思维方式实在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心灵需要,基于我们现时代存在的需要。我们只有认识到我们身处时代的这种心智物化状态,才有可能真正进入“历史”,才能利用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智慧。这种转换,有时需要庄子式的思维,比如在《秋水》篇中,庄子写道:“量无穷,时无止,分无常,始终无故”。庄子在这里用了一个“故”字,“无故”之“故”。这个“故”字就是我们上面分析的与“史”相对的“故”,也可以理解为“本来状态”。这种“故”(过去)是“恶乎往而不可哉?”,是“往而不反”的,是非静止、变动不居的。它即是老子所说的“道”(一阴一阳之谓道)、时间或历史。它是永恒的流动,即万法的虚空,现实世界中万物的变化,也即历史,不过是这永恒波动的表面现象而已,哪来什么本质?
老庄替我们转换过思想方式,但我们却依旧固守着故辙,这也算是一种历史的故智罢?!
作者:邓文初 公众号:一个思享家的走神